这个月,是杜拉斯一百岁了。这个灵魂和文字一样鬼魅的女人,一百岁了也照样是传奇。她死了仿佛她依然活着,活在她那些永不死去的故事里。当然,也活在她与扬惊世骇俗的恋情之中。扬,这个小她三十几岁的男人,又能怎么样呢?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男人可以和比自己小三十几岁的女人相好吗?
1975年,康城的某个电影院放映电影《印度之歌》。杜拉斯的电影。电影放完了,杜拉斯来参加一场讨论会,和观众见面。这个时候杜拉斯已经61岁了,声名显赫。还是大学生的扬也在里面。他的口袋里面装了一本书《毁灭吧,她说》。当然是她的。他要她给他签名。她签了。他对她说,我想给您写信。她写下了她在巴黎的地址。还对他说,可以照着这个地址给她写信。
 |
| 美女作家杜拉斯 |
扬有了这个地址:巴黎,第六区,圣伯努瓦路5号。第二天,他就开始写信,寄给这个地址。他写信,就再也没有停下。每天写,有时一天好几封。有时停下几天,接着又写。他给那个地址寄了几箱子信。他从来不指望她回信。这样的信一直写到1980年。写了6年。这一年,他接到了她的信:“我刚写完了一个剧本,我想其中有一段是为您而写的。我并不认识您。我读了您所有的信。我都留着呢。”他欣喜得要命,信写得更勤了。这一年的七月,他打给她电话:我是扬。她说,来吧,这里离康城不远,我们一起喝一杯。两个小时后,他去了那里。
她拥抱了他。她问他,为什么来。他说,为了相互了解。她觉得,在她生命的这一个时刻,66岁的这个时刻,有人这样大老远来看她,是件了不得的事。他又高又瘦。他们吃东西,喝酒,谈书,聊电影。当然,几乎都是她说,他听。她的声音有力,晴朗。他的声音柔和得难以置信。到了晚上,她对他说,你可以留下来,住在我儿子的房间里。房间面朝大海,她已经把床铺好了。第一天晚上,他住了单独的一间。第二天,他和她睡在了一起。他们做爱了。扬说,她的身体年轻得令人难以置信。他就这样留了下来,离不开她了。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她,直到她离世。
 |
| 传奇爱恋 |
杜拉斯曾说: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,会是个妓女。在《情人》里面她写道:我身上本来就具有欲望的地位,我在15岁时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,尽管我还不懂得什么叫逸乐。扬见到杜拉斯的时候,美已经离她而去,当然,那智慧的美还在她的身体里面。扬认得出这些。扬在没有见过杜拉斯的时候就已经认得出这些来。
她和他有过那样美丽的身体事件。扬想起他们的初夜。杜拉斯对扬说,来,别害羞,到我这儿来,我将向您展示我的躯体。来,抚摸我的身体。他照着办了。她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“对,再来,爱我吧,爱得更热烈一些”。她在对他说出召唤。他照办了。他只做她要他做的事。她的身上有一种野蛮的自由。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自由。这种自由附着在这个女人的身体上。这个身体在向他请求,想享受。几乎是在恳求:吻我吧。他被这样的感情弄得恐惧了。这个女人就是他的死神,她力量强大,是她创造了一切。她无疑有力量把他带到任何地方,任何一个她想要去的地方。带她去她想去的地方,是他的责任,也是他的愿望。那个地方同样也是他想去的地方。她的这种创造的力量同时使她创造出她的文字。这些文字使世界惊艳。对,就是这种力量让他臣服,并且痴迷。这个女人破坏了所有的等级。而这种破坏让他满足。他从此开始学习一个艰难的工作,那就是爱她。她索取了一切,他奉献了一下,完完全全。除非没有任何东西可索取了。她老了,腿脚不灵便。他就监看着她的一举一动,生怕她摔倒。晚上,她睡了,或者没睡,他会起床到她的房间里去,看看是否一切都好,看看她是否活着,是否还在那儿。
 |
| 他们的生活很甜蜜 |
她叙述,他记录,在打字机上。她说累了,他写累了,他们就到外面去。看海,看船,看海鸥。开着车去外面,他们会唱同一支歌。他们甚至在车里面把歌震耳欲聋地唱。她说,扬,我们唱吧。他唱走调了,管他呢。他们唱了几个小时,后来,必须回去了,得干活了,得写书了。他给她带去任务,那就是不让她停止写作。他把她的字落实到纸上。
杜拉斯是个难缠的女人,从来都是。她不是一个可以合作得很好的女人。她自恋,她嘟哝。她对扬说,告诉我,你能去哪里,你跟一个著名的、十分聪明的女人生活在一起,你什么都不用干,吃住免费,全世界的人都想取代你呢。事实上,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像扬这样,忍着她的乖戾。他果真有被惹火了的时候,对她吼:杜拉斯我受够了!杜拉斯我再也忍受不了了!杜拉斯结束了!她又会静下来,让他火,然后拉着他的手,说,不,别这样说,这不是真的,你跟杜拉斯决不会完,你知道这一点。是的,他们没完,没有停止,一切又重新开始,从来没个够,还不够,要爱得更热烈。
杜拉斯还是越来越老了。杜拉斯再强大,她也会老。这可真是没有办法,也毫无道理可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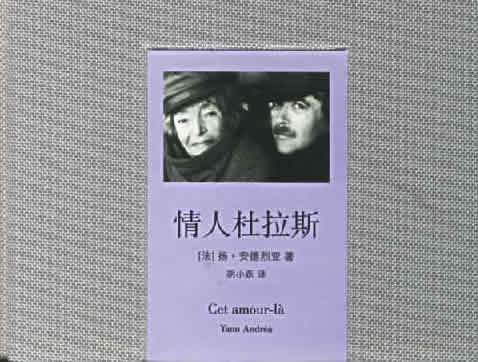 |
| 他们的爱情故事 |
死亡还是一天一天地朝着她来了。扬看着她一天一天虚弱下去。每天,他都觉得是她的最后一天。每天早晨,她还活着,这就是一个奇迹。1996年初,她对他说,杜拉斯,完了。扬没说话。他不想说什么安慰人的话。她说,完了,我再也不写了。扬说,这本书,应该把它写完,这本要消失的书,我们把它继续写下去。他低下了头,她也沉默。她离世的前几天,昏昏欲睡,什么也不能干。她站起来,想走到桌边去。就在那时,扬看到她的身体倒了下去,很慢很慢。他冲了过去,就在她的头要碰地的那一刹那,他用手托住了她的头,没让它碰到地上。她看着他,那目光分明在说:我爱你,胜过爱世上的任何人。他知道她爱他。最后的时刻来临了。杜拉斯半坐在床上,靠着枕头。她看着扬,对他说:扬,永别了。我走了。拥抱你。扬拥抱了杜拉斯。他说: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?你要去哪?为什么要说永别?杜拉斯的心脏慢慢地停止了跳动。那一刻,扬在她身边。她抓住他的手,又往上抓住他的臂。她紧紧地抓着,他感觉到她的手抓着他的皮肉。扬躺在一动不动的她的身边,他无能为力。那一天是1996年3月3日。
好长时间,扬没有走出杜拉斯留给他的那个居所。他不出门,只吃东西,吃得很胖,以至于长了四十多斤肉。没有杜拉斯,扬的一切也都结束了,他不想活了。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自己杀死。他看电视,什么节目都看,不加选择。他曾决定在窗口上吊。他在窗角用皮带系了一个圈,爬上一张椅子,把头钻进圈中。但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太重了,皮带会绷断的,或者会把窗框给拉下来。这不是个好办法。他想用枪杀死自己,但怎样去买枪呢?他这副样子怎么去买枪?他不洗脸,不刷牙,不洗头,脸也不刮了。几个星期都是这样。他脏兮兮的,旁边是成堆的报纸,成堆的酒瓶子。没有了杜拉斯,这个霸道的女人,扬不知道该怎么活。杜拉斯死前曾经对扬说:对我来说,死,没什么,但对你来说就严重了,你将发现,没有我的日子将很艰难,几乎难以忍受。这个自恋的杜拉斯,这一次还真是没有白自恋。对扬来说,她的离开让他确实艰难,远不止艰难。扬还想:“你呢,杜拉斯,没有我你怎么办,怎么在没有我的那个地方生活?没有任何人照料你,这我可以肯定,那里会变得跟我一样,乱七八糟,一片狼藉。”
杜拉斯死了三年之后,扬才试着出来走走。他为她写下了几百封信。现在他还在写,词都用光了,他还在写。他很高兴,他又可以给她写信了,这样他就能活下去了。写累了,他就往那所公寓打电话,像过去那样打给她。电话在空响。
后来,有记者问扬,这场爱情究竟是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?扬说:“不,这不是一场美丽的艳遇,这是一件非常……非常神秘的事情。
赵玫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叫《女人要的是什么样的男人》。
赵玫说,像约翰,像扬,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一类女人所需要的男人。我们这样的女人,当然是写作的女人,艺术的女人,灵魂尖锐又脆弱的女人。这样的女人在人生的青葱岁月,最容易迷恋的就是劳伦斯那样的男人,这样的女人在自己的青葱时代,不屑于约翰、扬这样的男人。但是,当女人们度过了青春期,经过了很多的岁月,我们才知道,懂得体贴、支持、帮助和有爱心的男人,才是我们理想中的。还要脚踏实地的,让我们感到那种真真切切的关怀和拯救。因为当有一天,我们老了,男人的成就和光辉便对我们毫无用处。我们要的只是能有一个爱我们的人,与我们心心相印地生活在一起。我们不求这样的男人经历我们的青春期,而要他们在我们更年期的时候与我们相守不渝。这很难。因为这是在我们失去了美丽之后开始走向衰落和死亡的时候。这是一个悲伤和悲壮的时候,仿佛日落。

